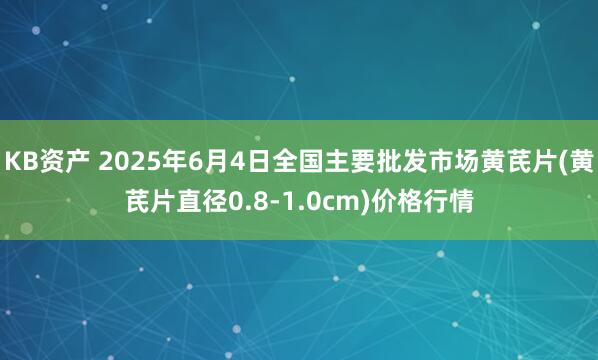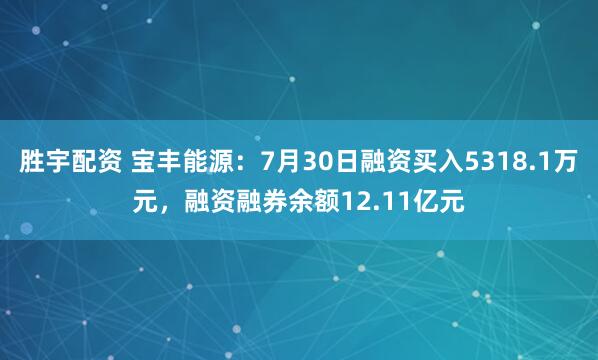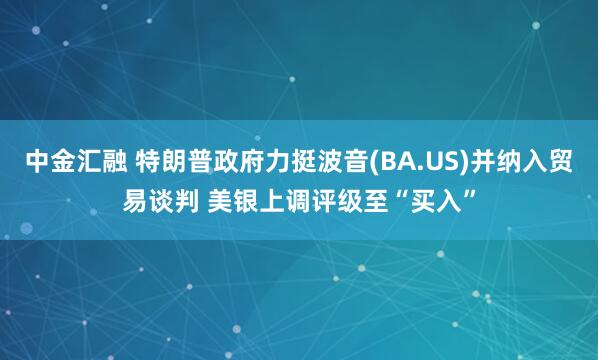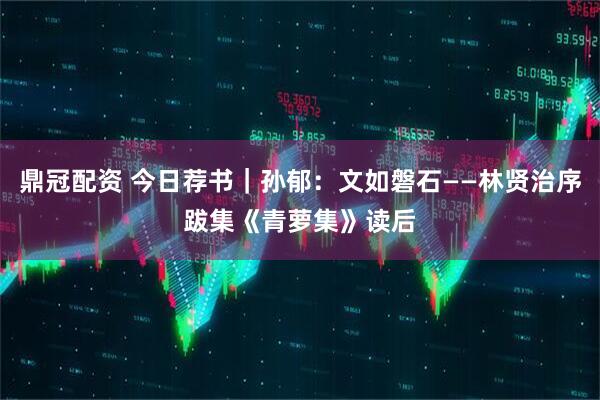
鼎冠配资
《青萝集》,林贤治著,花城出版社2025年出版
《青萝集》是林贤治新出版的序跋集,文章长短不一,可深谈的地方不少。这使我想起林先生的样子,三十余年间,我们的联系断断续续,然而印象深刻。他是很有个性的人,见面的时候,彼此有时候会发生一点争论,他对于我的一些写作,虽多有鼓励,但偶持批评态度。比如我对于“苦雨斋”的研究,他就不以为然,并提醒我警惕学院派的趣味主义。林先生不喜欢四平八稳,写作之于他,是一种思想的燃烧,而非自得其乐。他有一个观点,文人者也,过于象牙塔化,可能脱离现实,这样就远离了本真。所以他虽在文化界,却并不在热闹的地方。
序跋集一般都能够看出写作者的轨迹鼎冠配资,也是了解一个作者最好的参考文字。我过去读一些人的前言后记,觉得一本书的题旨大抵能够了解一二。好的序跋也可以作书话来读,是有文章之道的。黄裳、钟叔河的许多文字,都可以看出旧式文章的痕迹。但读林贤治的文字,完全没有书斋里的谈吐,有时如石击地,砰然有声。那些短短的文字,也同诗一般散着热气,闪烁的意象飘动起来,有回旋的意味在。
我最初读到的他的几本书,都与鲁迅研究有关。林贤治的写作一直在鲁迅的背景里,可以说辞章间不乏先锋意味。鲁迅影响他有几个方面,一个是批判意识,即对于流俗里病态遗存的鄙夷,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文本殊多。二是世界主义的眼光,所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可观,像东欧文学的读物,就曾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。三是对于现代经典的研究与出版,与一般的出版人不同,他的编辑理念,延续着五四那代知识人某些思路,关注创造性的思想的流布与人文精神的普及。四是行文中传染了《坟》《且介亭杂文》的阳刚之气,峻急与刚勇相间,也就是说,是深味文章之道的人,旧式文人的温吞之感是没有的。
看得出,林贤治写书与编书,其道一以贯之,那就是完成五四那代人的未竟之业。所写的《人间鲁迅》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《五四之魂》《娜拉:走出或归来》等,都非学院派的讲稿,而是有着野性之力,不被概念所囿,于反惯性的思维里打量远去的遗存。他很赞同以赛亚·柏林的观点,叔本华与尼采高于康德和黑格尔,因为前两人“反体系而返身于自由书写”。他对于中国知识界过于教条化的学术研究颇为不满,主要是看到诗与思的脱节,艺术与学术的隔膜。在他看来,如果不能在其间找到一条通道,还不如“返回创作,返回诗,摆脱灰色的理论,抛弃长期以来用逻辑语言建构的形式”。这也就与鲁迅思想重逢了,因为这位先驱者的写作与翻译,都是在激活思想,而非自囚己身。
在林贤治的写作里,知识分子的话题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他自嘲说,“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”,与自己是“不相宜的”。鲁迅在《关于知识阶级》一文中强调的是超越于利害的重要,而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可贵,大概就在这里。五四运动,其实是中国觉醒的知识人的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。他在《五四百年回顾丛书总序》里说,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“创世纪”,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就此开启。他礼赞五四的原因有多个,一是人的发现,二是世界的发现鼎冠配资,三是批判性,四是创造性,五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。他将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比作夸父式和堂吉诃德式的人物,都不无道理。理解了这些观点,也就看到了他的写作与编辑的使命是什么。而这五点也在他的文字中成了底色。
一个人的写作,总要经历多次的变化,或渐染杂色,或更为老成。林贤治则属于变中保持不变的人,外在的因素很难干扰自己的信念。也由此,他成了五四的护法者。《旷代的忧伤》《时代与文学的肖像》《一个人的爱与死》等书,都仿佛从《新青年》那里流出的声音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他虽然力主知识分子的精神,但不忘平民的根性。这使他一直与绅士、士大夫意识保持着距离。但这并不妨碍其精神的高贵之气的表达。在多年的写作中,他的资源主要不在古代文脉中,而是从五四和域外文学中获取灵思。他对于域外文学的兴趣很广,从莎士比亚到卡夫卡,从拜伦到波德莱尔,都能道其所长。而他自己就编辑了《哲学船事件》《流亡者之旅译丛》《曼陀罗译丛》等。域外文学中对于现实的穿透力的表达,和陌生化的词语的闪动,刺激了他对于生命叩问的尝试。
也因为这种开阔的眼光,和近于挑剔的词语表达,他的书写未尝没有唯美的痕迹。在他眼里,好的文章便是清透的思想的表达,惟有美的句子才配得上美的思想。阅读他的文字便会感到,很注重气韵的表达,句子起伏,情思流转,有时倾盆而下,有时则冷视片刻,那种不卑不亢的语调,有着一往无前的决然。域外的思想逻辑隐含在词语的背后,而翻译体的生硬感却被克服了许多。这种书写显示了他的独创性,一些作品翻阅片刻,即可知此为林氏文体也。
林贤治对于有着突围意识的写作者充满敬意。他与邵燕祥、王得后的友谊,便属此例。他们见面的时候,不都是和和气气,有时候也有观念冲突,不过都能理解对方,彼此互鉴。2018年,他编辑了随笔六种,收有王得后《刀客有道》,赵园《读人》,钱满素《觉醒之后》,筱敏《灰烬与记忆》等。这些作品在林贤治看来,作者们大抵有相近的价值取向,主张诚的写作,和思想的追问。他们有的是杂文家,有的是学者,但文字都气韵生动,“没有丝毫陈腐的学究气”。像筱敏的书,“所涉神话、传说、历史、人物和事件,包括阅读种种,充满隐喻,在人性道德的最高意义上,闪烁着诗意的光辉”。在他看来,随笔是思想的漫步,也是从俗谛中解放出来的神游。那些不规训的走笔,释放了精神能量,未被僵硬的思想所缚,这也正是中国最稀缺的一种表达。可以发现,林贤治编辑这套丛书,也是同行者的一次合唱。在中国知识界,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是极为可贵的,因为其间也可以看到当代另一种知识人的集体人格。
有几位朋友对于林氏的笔法持保留态度,主要是多见冒犯读者的地方,出语过重。我私下与朋友说,林贤治的偏执,也是他的书写策略。在远离流行语的地方凝视生活,给与世间的,往往是冷然之思。虽然峣峣者易折,但他却从风雨中一路走了过来,变成行路人的坚硬之盾。我们常人的选择与他有时大抵相左,亲近的是有些弹性的表达,觉得不必打开了一扇窗户又关上一扇窗户。但在经历了各种生活后,想起他的人与文,我有时也暗思,林贤治也许是对的。知识人不是水中的浮草,随波逐流,便会背叛曾钟情的信念。想起世上还有这种以鲁迅是非为是非的人,便觉得在我们的周围,文字的磐石并未消失。石在,火种怎么能灭呢?
鼎冠配资
大牛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